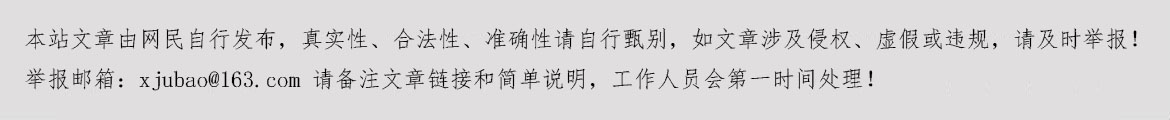这里的环境有多么恶劣?一位将军到达时含着泪说:“躺着就是奉献!”
卓拉长着“已婚脸”贾洪国
“米饭蒸不熟,氧气吃不饱;风吹石头跑,房顶被掀倒;六月春来早,九月雪花飘。”这首打油诗,生动描述了西藏边防哨所官兵的艰辛。
三十五年前到过卓拉采访,品着诗意的名字,走在艰难的路程!沿着山石铺就的台阶,吃力地向上迈越。石块的大小决定了台阶间隔的高低,在上面行走,需要的不仅仅是体力,更重要的是毅力。终于到达哨卡的顶部,那种疲惫极限之后的巨大喜悦,是一生中都无法体验的——只觉得嘴唇颤抖得厉害,狂跳不止的心几乎要从呼吸困难的胸膛中夺路而去!举目四望,荒凉遍地,怪石嶙峋,远处的铁丝网依山脚蜿蜒爬行,若隐若现;低垂的白云触手可及,耸立的哨所,悚然心惊。不远处,飒飒的晚风吟诉着千年的苍凉。
从头年10月到来年5月,近7个月冰封雪锁。海拔4687米的卓拉,藏语意为“怪石垒成的山峰”。位于峭壁之上,矗立云端,被称为“挂在天上的哨所”。冬季几乎与世隔绝,这里的戍边官兵如何度过漫长的封山期鲜为人知。和平时期的卓拉哨所,就是一场无边无涯地“厮杀”,对手是深不见底的苦寒寂寥,这是一种天高云远的“战斗”,沙场在寂寞清冷的国境边陲!
这里,一年只有两季——冬季和大约在冬季!
时值初夏,内地的热风没能越过绵延冰川,卓拉哨所仍在冰封雪裹封山之中。
在群山与天空之间,雪原是唯一的色彩。唯一能感知到寒冬的结束,是背运物资的官兵看到从积雪中探出头的雪山杜鹃。生长在海拔4000米的灌丛中,雪山杜鹃从这里向你道别,仰望你一路爬向哨所。
哨所266级台阶下面,是一个雪水汇聚成的“天池”,没有雨水、雪水的日子,官兵们要从湖里背生活用水。“哨所在山顶,生活用水‘雨天接雨水,下雪化雪水,没有雨雪就背水’,背一趟水要2个多小时。
白色的雪很美,但到过卓拉后会让你绝望,一年到头,卓拉有大半时间被雪拱卫。也因此,官兵们对雪有了更深的感情——铲雪、堆雪、滑雪、打雪,成了卓拉独有的体能训练方式;抗寒抗缺氧训练意味着要等雪融化成水,好来练习憋气;猫在雪洞里放松的时刻,是官兵生活中的一点吉光片羽。
苍山负雪,明烛天南,单调的雪也变得艳丽起来。
在至尊至敬的哨所面前,我心甘情愿做着它的俘虏。回忆中时常响起一句话:“站在哨所和守卫着哨卡的战士,无疑都是命运的英雄。”
卓拉哨所处在北印度洋暖湿气流与喜马拉雅山脉寒流的交汇处,雪多雨多雷多,常常是早上阳光明媚,下午电闪雷鸣。
一脚踏上哨所,仿佛登上了天空之城。但这方纯净之地,总迎来意外之客——在卓拉哨所,让官兵们心有余悸的不只狂风暴雪,还有不期而遇的雷暴,雷沿着电线和铁丝下来,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进屋“巡视”一圈,又转瞬即逝。用手机的时候怕被“雷劈”不是个笑话,哨所的军线电话也被打烂过好几部。后来,官兵只要一听见打雷声,就切断电源、关闭手机,在木床上围坐成一团。“霹雳哨所”因此得名。
这里一年无四季,一天有四季,年均气温低于-5℃!官兵们说,“这里天无一日晴、雪无一日停,一年一场风、从春刮到冬。”
哨所最不缺的就是雪。高原气候多变,山脚晴空万里,半山腰可能大雨倾盆,到山顶却是暴风雪。
平日里,战士们最常做的就是“打雪”,用雪水来烧水,洗漱、洗衣……现在条件改善,饮用水靠山下送纯净水,但生活用水还是靠雪水。官兵们从屋檐上接了导管,融化的雪水“滴答滴答”流进一个大铁桶里。
若从高空俯视,卓拉哨所像戴在雪山上的王冠,而鲜艳的国旗如镶嵌在王冠上的红宝石。
卓拉哨所是什么颜色?官兵军装的绿色。哨所海拔高、气温低,植被难以存活,军装是唯一的绿色。
这是他们守护的颜色,也是卓拉哨所最绚丽的颜色。
思绪有天生的一股渴望和欲望,尤其对于这威严的哨所,我绝不甘将自己灵魂的海拔降低如此低矮。
索道建好之前,每隔一段时间,他们要下山“背菜”、背物资。每年大雪封山前,他们还要“冬囤”。徒步攀爬雪山运送物资通常需要5个小时,官兵们负重爬冰卧雪穿过“忘乡坡”、“忘情坡”、“忘忧坡”3个危险的陡坡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官兵们离天很近,却离家很远。
山上信号不好,若有若无。闲时,他们登上山脊打电话。电话那头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女朋友已经数月、甚至几年未见。
从四面八方来到祖国西南,官兵吃菜的口味也变得“西南”。炊事员总是想着法子给大家做家乡菜,往往做到最后才发现,不过是把几种食材“放一起用辣椒炒”。即便被辣得通红,在官兵脸上也不大能看出。这点辣,驱寒去潮,哨所官兵一年四季都戒不掉。
喜马拉雅的内核仿佛永远冷硬,冰封了春意,却阻止不了戍边官兵的脚步。他们身着那抹松枝绿守在那里,天上哨所就有了春天,苦寒边关也有了色彩。
5月的内地鲜花盛开,但卓拉山口依旧冰雪覆盖,步行到卓拉哨所,要翻越三个陡坡,第一个是近70度的陡峭雪坡,在厚达几十公分的雪地里向上攀爬,考验着大家的体力和意志。陡峭的山坡,深厚的积雪,稀薄的空气,这条路是半个世纪以来卓拉哨所的生命补给线。
那年去卓拉山口巡逻,边防办公室的翻译说,你们的车上不了山,得用我们的“猛士”才能上去。那语气,根本不容置疑。
上山的途中,一路冰雪,驾驶员开得很慢。说“上”卓拉其实不准确,应该是“爬”卓拉才对——路上要翻越四个大山坡:一号坡陡,二号坡长,三号坡四号坡最让人背发凉。
上山的途中,遇见一个大石头,有多大呢?两层楼那么高,一间房子那么大。就那样横在路中间。没办法,我们只能从另一条更难走的小路绕过去。
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内地的三分之一。“在过去,你知道啥是西藏边防的‘四大名菜’吗?土豆、白菜、海带、木耳。‘四大名菜’要从每年的十月份吃到来年的五月份……”脱水菜,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,在雪水的浸泡下,膨胀成赭色的浆团,炒或熬以后,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。
如今,这些都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。
2013年盘山公路修通,2018年索道建成,让哨所基本物资补给有了保障,但还是容易受到天气影响。
如今的卓拉哨所,自然环境没有变化,但是,哨所的住房、用电、吸氧、洗澡,特别是物资运输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
改变的不仅仅是医疗条件,还有硬件设施。一栋三层保温哨楼,有阳光棚、洗浴室、存储室、娱乐室,并配备暖气、风能发电等设施。但永远不能改变的,依然缺氧、潮湿,悬在天边边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。
过去往山上运物资,需要四五名官兵每周运一趟,肩扛手提,在陡坡上攀爬;如今有了索道,每天都可运送,一趟只需半小时,一次可运送100公斤左右的物资,官兵们只需在哨所门口等着就行,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守防和巡逻上了。
索道的建成,不仅方便物资运输,还增强了一线哨所的医疗保障能力。2018年夏季,卓拉哨所一名战士突发高原肺水肿,昏迷不醒。官兵们通过索道将这名生命垂危的战士安全送下山,及时挽救了他的生命。
卓拉哨所自然环境恶劣,常年大雾弥漫、风雪肆虐,官兵不同程度出现心脏肥大、痛风、早衰等高原病症。西藏军人特有的“高原发际线问题”,在卓拉守卫者身上暴露无遗。猛然会面,个个看上去都会老10岁。“未婚”的他们羞于让外人看见他们的手。白雪皑皑中,哨所官兵黝黑的面庞颇有“辨识度”。
战士上到哨所,就不对妈妈说实话了。发照片的时候要“摆拍”场景,让妈妈看到自己“生活得很好”。美颜功能在这里也有了用武之地——借着滤镜“磨皮”,美化紫外线造访过的痕迹,让自己看起来像“重返18岁”。
但这些只是徒劳。相貌比年龄更为苍老,那是岁月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隆重印痕。这群“毛头小子”在离家最远、离天最近的地方,许多官兵都长了一张“已婚脸”。
“上了边防线,就要做奉献。”建立在理性和价值上的选择,让哨所官兵找到了巡边守关的感觉,从而无悔地走进风雪肆虐的世界。
“我从哪里来,将向何处去?”在这片热土上,边关将士寻觅到了寄托人生理想信念的灵魂家园,寻觅到了寄托光荣和梦想的精神故乡。
有位哨长的女友是他的同学,毕业时许多如胶似漆的情侣因为时空距离选择了分手,而他却带着女友永远相爱的誓言,自信而又甜蜜地奔赴边关,一年后,女友的誓言仍然铮铮,两年后誓言仍然铿锵有力,三年后女友的誓言终于被边关大门撞得粉碎:“三年了,我过生日你不能陪,我理解;我生病需要照顾你不在身边,我能理解。可我问你什么时候离开边防回到我身边,你却始终没给我答案。我不要你有多高的地位,不要你有多少钱财,我只需要你在我身边,这点要求不算高吧,但你却始终做不到。”
“我不想过两地分居的生活,现在我提建议供你选择:一是你脱军装转业。二是分手。你慎重考虑,我等你决定。”说完女友哭着跑开了。那一夜,他失眠了。躺在床上想了很多。都市那么繁华,女友是那么美丽深情,这一切都具有非常的诱惑力。可是到边防去是祖国的需要,是组织的决定,作为军人,在关键时刻怎么可以临阵退缩呢?从小时候向往军营开始,他心里对边防军人就有一种虔诚的膜拜。“边防”这两个字,是他心中的图腾。
都说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,但这位哨长和女友的爱情却始终没有越过边关,他担任了四年哨长,终于失去了相恋多年的女朋友。古人云:“存天理,灭人欲。”边防官兵牺牲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,恪守的就是戍守边疆这个质朴而又崇高的天理。因为他们认为,多彩的青春很美丽,奉献的青春更有价值。
在边关、战斗在云端,用青春热血谱写出一曲曲英雄赞歌。作为新时代老西藏精神传人,卓拉哨所官兵,继续在祖国西南边防用忠诚铸就起钢铁防线!
这就是我心中的哨卡,一个边防军人心中永远彪悍、永远壮美的图腾。如今,当人们谈论起边防,提及哨所,忍不住将它作为闲暇之余聊作游兴的景观,我的心中便隐隐有一股酸楚的痛。作为边防军人,卓拉哨卡已经成为我们曾经亚东军人心中巍峨的丰碑。
(注:本文中插图由仲建军提供!)
作者简介:
贾洪国:1968年生人,属猴好动!西藏军旅生活五年,成都县报记者十年。出版有个人文学集《一花一世界》、《人生足迹》、《风兮雨兮》。曾获得1992年全国《农民报》好新闻一等奖,三十多年来,在各类杂志、报刊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杂谈一千多篇。近年来,主要精力用于采写《寻访战友故事集》,目前已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初稿创作。因为“人在变老,军旅的记忆却永葆青春!”
作者:贾洪国